“快看,是易耀彩!”——1966年7月,泰和县禾木村的晒谷场边,几个放牛娃一声招呼炸开了锅。一个身着浅色军装、左臂挽着夫人的中年将领,正沿着田埂快步往村里走。阳光下,他的神情激动又局促海龟网,像第一次走出校门的年轻人。

部队专车停在村口,他却坚持步行回旧屋。“我想踩踩这条路的土,闻闻稻谷味。”易耀彩扭头对范景阳轻声说。妻子点点头,没有作声,她知道丈夫心里装着三个人:早逝的父母,还有那位在户口簿上写着“收养”却被乡亲们喊作“童养媳”的张凤娥。
禾木村人并不多,巷道弯弯曲曲。村头一棵老樟树见证过易家几代人的悲欢。此刻,张凤娥就站在树下,抹着围裙,浑身微微发抖;她不敢往前迎,只小声重复一句:“他真的回来了?”待易耀彩走到她面前,他先是敬了一个军礼,接着笑着开口:“老姐姐,我们来看你来了!”短短一句,打碎了张凤娥多年压在心口的石头,她的眼泪刹那决堤。
这一幕若倒回五十年海龟网,完全是另一种光景。1916年,易耀彩出生在这里,家境寒苦却书声不断。十岁那年,他放学回家,母亲多端了副碗筷,对他说:“这是张凤娥,以后叫她姐姐。”乡下孩子心思单纯,他只把对方当家里新来的玩伴。可村里的老人早已私下议论:那是给小易定下的童养媳。

再穷也要读书,父母舍不得让儿子幼时下地务农。可形势突变,1927年井冈山的枪声传到了禾木。农民运动一潮高过一潮,易家两位长辈先后加入赤卫队。年仅十四岁的易耀彩,被舅舅一把拉进了红军队伍。这一走,家门就被时代的洪流淹没。
之后的十多年,是枪林弹雨与尸骨腐草。赣江血案、长征饥寒、百团大战、解放战役……易耀彩从列兵到旅长,再到少将。身上多了十几道疤,心里却始终惦念禾木的炊烟。但他没有想到,父母早已横尸于乡团的铁枪之下。消息辗转传到前线时,他握紧拳头,整整一夜未合眼。翌日上战场,他一句话未说,所有人都说那天的易旅长像一把亮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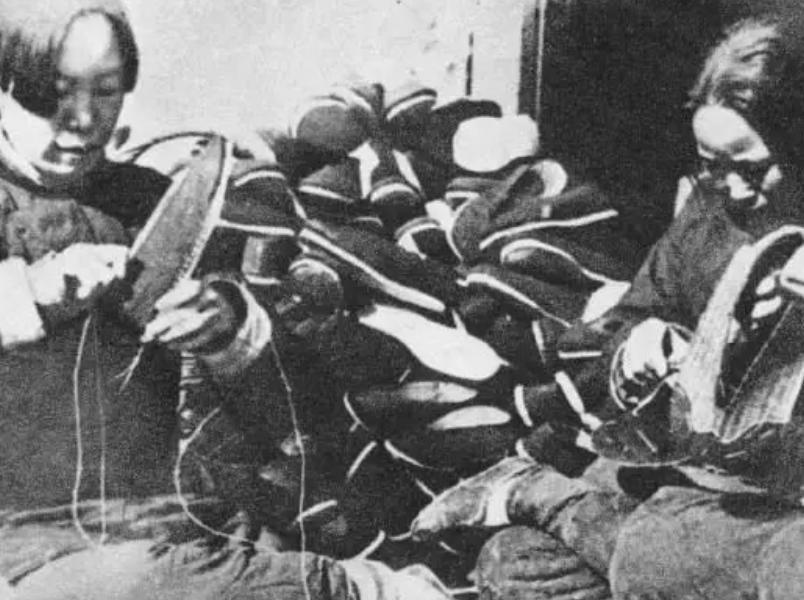
父母遇难的真相,还是张凤娥替他收拾残骨时查明的。敌人看她是个瘦弱女子,懒得多费枪弹,只把她赶回娘家。张凤娥就这样活了下来。她没再改嫁海龟网,种田纺线,逢年祭日悄悄给易氏祖坟除草。村里人劝她再寻归宿,她只说:“我要帮他看家。”
1940年春,太行山深处的军分区来了位十七岁的小护士——范景阳。她行事爽利,药箱背得比男兵还稳。一次炊事班做饭缺盐,她愣是翻山跑了二十里把盐背回。易耀彩注意到这个姑娘,用口琴跟她合奏了一首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。没想到第二天组织科就催婚,理由也直接:“前线没有谈恋爱的条件,先结婚再慢慢磨合。”范景阳嘴上直说“太仓促”,心里却并不排斥。两人就这样把一纸婚书压在行军图里,继续打仗。

抗战胜利后,通信条件好了一些。1946年的一个黄昏,易耀彩写下久违的家信。他用极小极小的字,向张凤娥说明自己已婚,请她自由择偶。信寄出后,他坐在军营门口抽了三支烟。多年羁旅,风霜刻在眉间,他对范景阳说:“她等我,是不应该的。”范景阳拍拍他的肩,只留一句:“人各有坚持。”
1955年授衔典礼,照相机咔嚓一声定格荣光。台下鼓掌的人群里,没人知道这位少将仍记挂一个低调的农妇。直到1966年探亲,他终于兑现承诺。那天,他把军功章交给生产队保管,又用自家津贴给张凤娥添了新被褥。临别前,他掏出一枚小口琴递过去:“小时我练的,就是这支。”张凤娥接过,嘴唇哆嗦,终究没有吹响。

时间推到1986年,泰和公社搞农田改造。易耀彩夫妇回乡第二次探望张凤娥。雨后田埂泥泞,他坚持不用公社吉普,和二十年前一样步行。张凤娥已经佝偻,他将干粮袋递过去:“姐姐,身体要紧,钱不够就写信给孩子们。”两个老人相对,雨丝打在屋檐上,没人再提旧事。
1990年夏末,易耀彩病逝。安葬地选在禾木的丘陵,他生前留下话:“落叶归根。”六年后,张凤娥也谢世。范景阳作出一个让全村震惊的决定——把张凤娥葬在丈夫旁边。她淡淡解释:“她守了一辈子,我们欠她一个归宿。”旁人听后,心里五味杂陈。
再后来,泰和县修起了纪念馆,其中摆着一双旧草鞋、一条裂口皮带和那支小口琴。解说员常补充一句:“草鞋走完二万五千里,皮带熬过命悬一线的疟疾,口琴见证了三个人的守望。”游客大多只惊叹名将传奇,却极少有人留意展柜角落那张泛黄的乡亲名单——排第一的,是张凤娥。

历史的书页厚重,真实的感情却简单——一句“老姐姐,我们来看你来了”,成了易家堂屋永远的回声。
股联社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